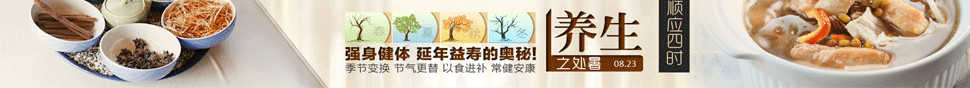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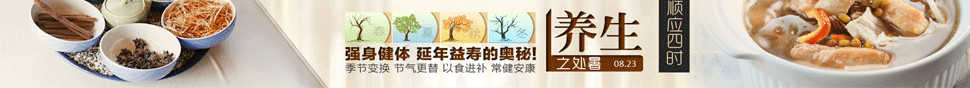
点击上方蓝字,订阅文艺批评▼
编者按
在充满断裂和翻转的20世纪,中国少数读者通过60年代“内部发行”的《爱伦堡论文集》和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了解到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和她的诗歌。爱伦堡在写于年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和回忆录里对茨维塔耶娃思想情感、诗艺的矛盾性,和“极端的孤独”性格有精彩的论述。另外,爱伦堡在论述中还触及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极端孤独”的茨维塔耶娃呈现为对矛盾的处理过程。她离不开艺术,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同时对艺术的权力也始终保持怀疑。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通过60年代张孟恢所译的爱伦堡文集和回忆录对中国诗人多多和张枣产生影响。两位诗人分享、继承了茨维塔耶娃的诸多表达和情绪。而多多和张枣也同样影响了读者对茨维塔耶娃的阅读。
感谢作者洪子诚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洪子诚
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文学论文,(苏)爱伦堡写于年,中译收入“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之一的《爱伦堡论文集》,张孟恢译,世界文学编辑部年编辑出版,内部发行。
阿赫玛托娃在年代的中国
现在被高度评价的俄国20世纪初的一些作家、诗人,在中国当代的五六十年代却很受冷落,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介绍,大多数人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不过,阿赫玛托娃可能是个例外。原因是年,苏联作协机关刊物《星》和《列宁格勒》,刊登了左琴科的小说和阿赫玛托娃的诗[1],它们被认为是“无思想性”和“思想有害”的作品。这引起苏共中央的愤怒,联共(布)中央于年8月14日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紧接著检查自己的错误,开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出作家协会,解除吉洪诺夫的作协主席职务,并改组苏联作协。随后,苏共掌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9月在列宁格勒“党积极分子会议和作家会议”上做了长篇的批判报告[2]。这些报告和文件的中译,连同30年代的苏联作家会议章程,以及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收入《苏联文艺艺术问题》[3]一书:这本书50年代初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被中国作协列为重要参考文件,所以文学界许多人知道阿赫玛托娃的名字。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对阿赫玛托娃创作定下的基调是:
……她的文学的和社会政治的面貌是早为苏联公众所知道的。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渗透着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表现着那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
日丹诺夫的报告对这一思想艺术倾向有具体的描述。与现在中国(俄国那边大概也是这样)对“白银时代”文学的主流看法相反,日丹诺夫的评价是:
高尔基在当年曾经说过,到这十年,够得上称为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可耻和最无才能的十年,从年革命之以后,知识界大部分都背叛了革命,滚到了反动的神秘主义和淫秽的泥坑里,把无思想作为自己的旗帜高举起来,用下列“美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叛变:“我焚毁了自己所崇拜的一切,我崇拜过我所焚毁了的一切。”……社会上出现了象征派、意象派、各种各样的颓废派,他们离弃了人民,宣布“为艺术而艺术”的提纲,宣传文学的无思想性,以追求没有内容的美丽形式来掩盖自己思想和道德的腐朽。
这个描述,经历那个年代的人相信并不陌生;而阿赫玛托娃,日丹诺夫说,她是“这种无思想的反动的文学泥坑的代表之一”——
(她的诗的)题材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她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贵妇人的诗歌,它的范围是狭小得可怜的。她的基本情调是恋爱和色情,并且同悲哀、忧郁、死亡、神秘和宿命的情调交织着。宿命的情感,——在垂死集团的社会意识中,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死前绝望的悲惨调子,一半色情的神秘体验——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的精神世界,她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的旧喀萨琳时代”古老贵族文化世界的残渣之一。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阿赫玛托娃
因为涉及20世纪初俄国思想界和诗歌界的状况,日丹诺夫报告中也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他的名字当年译为“欧西普·曼杰里希唐”。译者曹葆华所加的注释是:“俄国阿克梅派的代表诗人,其作品十分晦涩难懂”。日丹诺夫说,阿克梅派的社会政治和文学理想,在这个集团“著名代表之一——欧西普·曼杰里希唐在革命前不久”的言论中得到体现,这就是对中世纪的迷恋,“回到中世纪”:“……中世纪对于我们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具有着高度的界限之感。”“……理性与神秘性的高贵混合,世界之被当作活的平衡来感受,使我们和这个时代发生血统关系,而且鼓舞我们从大约年在罗马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作品中吸取力量。”日丹诺夫认为,阿赫玛托娃和西普·曼杰里希唐的诗,是迷恋旧时代的俄国几万古老贵族、上层人物的诗,
这些人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除了怀念“美好的旧时代”,就什么也没有了。喀萨琳时代[4]的大地主庄园,以及几百年的菩提树林荫路、喷水池、雕像、石拱门、温室、供人畅叙幽情的花亭、大门上的古纹章。贵族的彼得堡、沙皇村、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与其他贵族文化遗迹。这一切都沉入永不复返的过去了!这种离弃和背叛人民的文化渣滓,当作某种奇迹保存到了我们的时代,除了闭门深居和生活在空想中之外,已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一切都被夺去了,被背叛了,被出卖了”。……
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和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描述,也就是中国当代“前三十年”对这段历史的基本看法。不过,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学界和诗歌界占主流位置的评价出现翻转,基本上被另一种观点取代。这种观点,回顾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时代亲历者别尔嘉耶夫[5]的描述。按照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的说法,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颇为复杂:在20世纪初,他“既承认革命行动是合理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又主张神秘主义,而反对革命行动。他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走了相反的道路,开头信的是他们,后来却回到费尔巴哈的立场上”[6]。这位矛盾的神秘主义者的描述,显然与日丹诺夫大相径庭,包括所谓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等:
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没有创作与19世纪长篇小说类似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但是却创作了非常出色的诗歌。这些诗歌对于俄罗斯意识,对于俄罗斯思潮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是个象征主义的时代……(象征主义作家)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新的潮流并且处在与旧文学的代表的冲突之中。索洛维约夫的影响对于象征主义的作家起了主要作用。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表达象征主义的实质: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只是反光,只是阴影,
来自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象征主义在所看到的这种现实的背后看到了精神的现实。……象征主义者的诗歌超出了艺术的范围之外,这也是纯粹的俄罗斯特征。在我们这里,所谓“颓废派”和唯美主义时期很快就结束了,转变为那种以为着对精神方面寻求的修正象征主义,转变为神秘主义。……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和诗歌具有精神崇拜性。诗人—象征主义作家以他们特有的敏感感觉到,俄罗斯正在跌向深渊,古老的俄罗斯终结了,应该出现一个没有过的新的俄罗斯。……[7]
20世纪的历史最不缺乏的是裂痕,是断层的沟壑,情感、观念的急剧翻复是家常便饭。不能预见今后是否还会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阐释转换。值得庆幸的是,阐释所需要的材料、资讯将会较容易获取,不像中国当代“前三十年”那样,在日丹诺夫指引下曾“恶毒地”想象阿赫玛托娃,而她的诗我们读到的,只有日丹诺夫报告中所引的那三行:
可是我对着天使的乐园向你起誓
对着神奇的神像和我们的
热情的夜的陶醉向你起誓……
(阿赫玛托娃:《AnnoDomini》)
爱伦堡带来的茨维塔耶娃
到了60年代,中国少数读者知道了茨维塔耶娃,以及曼德尔斯塔姆的名字。并非翻译、出版了他们的作品;他们是爱伦堡带给来的。年,《世界文学》编辑部编选了作为“世界文学参考资料”的《爱伦堡论文集》。集中收入爱伦堡写于年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8],其中谈到茨维塔耶娃等人的生活和创作。这两种书,都属于当年内部发行的“内部读物”:也就是政治和艺术“不正确”供参考、批判的资料性读物。
伊利亚·爱伦堡
《人,岁月,生活》年版
爱伦堡年去世,晚年主要精力是撰写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年开始在苏联的《新世界》杂志连载,很快在苏联和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据中译者说,“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十分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anbaicaoa.com/sbcfb/8831.html

